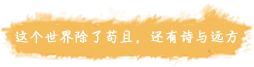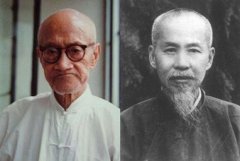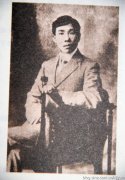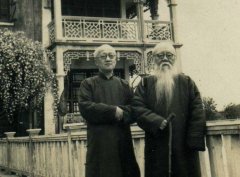【作品提要】 沃谢夫因耽于思考被机械厂解雇了,不得已来到城外,加入了挖掘基坑的队伍。工程师普罗舍夫斯基、队长奇克林等人都在全力以赴地摧毁大自然古老的结构,建一座独特的供全体无产阶级居住的大厦。身体病弱的科兹洛夫一心想在组织工作方面做出成绩,...
【作品提要】 红军女战士马柳特卡出身于一个渔夫家庭,父母双亡。她为人善良,富于幻想,对诗歌非常感兴趣。她枪法如神,被她击毙的白军已有四十个。在一次撤退中,仅有二十三人生还,马柳特卡是女战士中仅有的幸存者。随后他们在一次行动中捉了一个白军中尉...
【作品提要】 医学教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科学试验: 为小狗沙里克移植了流氓无产者丘贡金的脑垂体。手术成功了,沙里克逐渐脱去了狗型,变成了人——沙里科夫。但是,变成人之后的沙里科夫不仅保留了狗的习性,还具有了丘贡金的流氓习气——...
【作品提要】 动物学教授佩尔西科夫偶然发现用一种神奇的红光照射生物可以使其以惊人的速度生长与繁殖。这一尚未成熟的科学发现被一个急功近利的国营农场经理草率地应用于小鸡孵化,以期振兴国家的养鸡业。结果却是阴差阳错,事与愿违,佩尔西科夫教授订购的...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青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
沈从文是个写文章的人。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写文章的人不就是作家么?不,这并不一定就是一回事,我在中学里就开始读沈从文的文章了。读过《边城》、《湘行散记》,觉得很喜欢。他的小说我读得不多,可是我知道他写得很多。他的小说我也并不是篇篇都喜欢。他...
××: 从南京回来已经四十多天了。在手提包里带回了一册日记,上面记着几天来的游踪、见闻,还有一些零碎的感想。这大半是每天深夜在旅舍的灯光下记下的,零乱得很也简单得很。至今还保留着新闻记者的习惯,无论走到哪里,随身总带着一个小本子,时时要记点...
我们到南京时是一个风沙蔽天的日子,下关车站破烂得使人黯然。站外停着许多出租汽车,我们坐了其中的一部进城去。原想借这冒牌的“华胄”的风姿可以有点方便,不料车到挹江门时仍得下车接受检查。这职务是由“宪兵”执行的,严格得很,几乎连每一个箱子的角...
温馨的、有点潮湿的、南方的夜降落在城市的林梢和屋檐前。一枚新月好像一朵橘子花,宁静地开放在浅蓝色的天空中。 城市在闪耀着它的宝石似的光辉,散发着豆蔻一般的香味。泉州,你经历过多少风险,珍藏了这样多的瑰宝?呵,那林立的碑坊,那雄伟的东塔和西塔...
我看见一棵榕树。它美丽得好像开花的土地。它的树干好几个小孩子手携手来才能围抱...
自从有一天,和他因小事争吵,我一怒离家,回来时却发现忘带钥匙,又不肯按铃请他来为我开门,只得索性坐火车去高雄住了一夜。那以后,我对钥匙就十分小心。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自尊的保障,独立的象征。代表着可以我行我素的自由,和不必求助于人的...
一、 雪 生长在南国的孩子,你见过雪吗?你爱雪吗?也许曾点缀于你生活篇页上的,只是碧于天的春水吧? 在我的故乡,到了冬季,是常常落雪的,纷纷的雪片,为我们装饰出一个银白的庭园。树,像是个受欢迎的远客,枝上挂了雪的花环,闪烁着银白色的欢笑。 我喜欢...
“夏木荫浓”,这是三十年代我投考江苏省立常州高中时的作文试题。当时感到这题目太深奥,很难发挥。因之我每见到浓荫的树木,总会联系到那试题,想从中悟出点什么道理来。一直到学习艺术后,才深深体会到树木之美,其浓荫之迷人,但并未思索其哲学含蕴。 童...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清早,从清凉山上望下去,见有不少的人,顺山下大路朝东门外飞机场走去。我们《解放日报》的同志,早得了消息,见博古、定一同志相约下山,便也纷纷跟了下来,加入向东的人群,一同走向飞机场去。 人们的心情很不平静。近两个星期来形...
我在西双版纳的美妙如画的土地上,幸运地遇到了一次真正的蝴蝶会。 很多人都听说过云南大理的蝴蝶泉和蝴蝶会的故事,也读到过不少关于蝴蝶会的奇妙景象的文字记载。从明朝万历年间的《大理志》到近年来报刊上刊载的报道,我们都读到过关于这个反映了美丽的云...
海洋,多么的无边无际,辽阔深邃!这是世界上一切生命的发源地。这是地球上最巨型的动物的藏身之所。陆地上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海洋完全可以把它淹没。地球上有四分之三的区域都是海洋。你凝视着海洋,有时真和望着星空一样,会涌起一种思索时间和空间的微妙、...
我们生活在一个开辟人类新历史的光辉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对许许多多的自然景物也都产生了新的联想、新的感情。不是有无数人在讴歌那光芒四射的朝阳、四季常青的松柏、庄严屹立的山峰、澎湃翻腾的海洋吗?不是有好些人在赞美挺拔的白杨、明亮的灯火、奔驰...
早在十年动乱的前两年,我由于受到“中间人物”事件的株连,已经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而处于“靠边站”的状态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间发表的。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回编辑部上班,在家里过着“员外郎”的生活。“员外郎”的生...